小核酸药物QPI-1007被用于治疗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NAION),同时具有治疗青光眼的潜力。本次批准的是针对NAION的国际多中心II/III期关键研究,此前QPI-1007已被美国FDA认定为孤儿药。QPI-1007是获CFDA批准中国临床试验的第一例小核酸药物。该药物在中国以及亚洲区域(除少数特定国家外)的开发和市场权益由注册于昆山小核酸基地的昆山瑞博夸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瑞博夸克")承担和持有。瑞博夸克是中国小核酸制药领域的领军企业苏州瑞博和世界小核酸制药的领军企业美国Quark公司基于强强联合的理念共同组建的专注于特定小核酸药物研究和产业化的制药企业。
苏州瑞博董事长梁子才博士指出,小核酸制药是人类现代制药历史上的继小分子药物、单克隆抗体和蛋白药物之后的第三次浪潮。中国在小核酸技术上多个方面处在与世界同步的水平,我国首个小核酸药物临床试验的启动是中国小核酸制药产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推进中国在此领域的研究和产业化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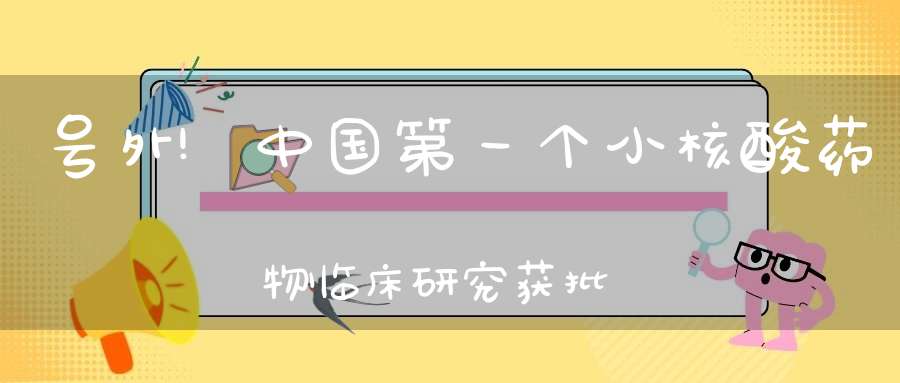
Quark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DanielZurr博士表示:"此次QPI-1007的临床试验在中国获批,是Quark团队和瑞博团队通力合作达成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接下来我们将在瑞博夸克的框架下,加大引进VC资金的力度,力争将多个小核酸药物推进到临床试验阶段,开拓亚洲小核酸药物市场"
QPI-1007已经确定由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王宁利教授主持。对于QPI-1007临床试验的获批,王宁利院长表示:"QPI-1007本质上是一个视神经保护药物,包括NAION和青光眼在内。视神经损伤相关的眼科疾病很多,对视神经保护的药物在临床上有巨大的需求,但是至今没有一种真正能对视神经具有保护作用的药物面世。QPI-1007在前期临床试验中已经表现出在这方面的潜力。我期望各方同心协力,早日完成临床试验,如果安全性和有效性均能达到预期指标,则可使病人早日受益。"
关于小核酸
RNA干扰(RNAi)现象的发现是过去15年来生命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之一。RNA干扰的效应分子是一种短双链RNA,即小核酸(siRNA),可在包括人类的多种细胞和组织内发挥强大的基因沉默效应。siRNA疗法开发是目前生物医药领域的前沿和热点,广泛地被认为极有可能在未来20年内为制药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关于瑞博夸克
2012年9月,苏州瑞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美国Quark制药公司正式宣布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并成立昆山瑞博夸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在中国和亚洲推进小核酸药物的临床试验和产业化。
关于苏州瑞博
苏州瑞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总部位于江苏昆山小核酸基地,是致力于开发小核酸药物的创新型研发企业,是中国小核酸技术和小核酸制药产业的主要开拓者。公司围绕小核酸药物开发的技术特点在小核酸靶点序列设计和化学修饰、候选药物筛选、递药载体、药效药理评价等各方面建立起完善的小核酸创新药物研究体系;拥有小核酸中试生产、制剂生产、CMC研究的设施和技术。通过自研和国际合作形成了丰富的小核酸药物品种研究管线。
关于美国Quark制药公司
Quark制药公司是RNAi技术研发领域的国际领先企业,拥有行业内最为丰富的临床阶段siRNA品种线。该公司整合的药物研发平台贯穿了靶点识别到药物研发阶段。Quark的递送技术可将siRNA递送至多个组织和器官,包括眼睛、肾脏、耳朵、肺、皮肤、脊髓和脑部。Quark拥有三个siRNA临床阶段候选药物,分别应用于五个不同疾病适应症,其中两个药物正处于关键的III期临床研究阶段。Quark在中国的合资公司-昆山瑞博夸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为Quark全球临床研发共同参与者。Quark总部位于美国加州Fremont,分别在科罗拉多的Boulder和以色列Ness-Ziona拥有研发机构。
达安基因:与LifeTechnologies合资成立的广州立菲达安诊断产品技术有限公司宣布正式启动基因测序分子诊断项目。广州立菲达安诊断公司是LifeTechnologies除北美外、在全球设立的唯一一家合资公司,总部设在广州。公司是以分子诊断技术为主导的,集临床检验试剂和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全国连锁医学独立实验室临床检验服务为一体的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公司在分子生物学技术方面,尤其是基因诊断技术及其试剂产品的研制、开发和应用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目前主要从事荧光PCR检测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以及荧光PCR检测试剂盒的生产和销售。
双鹭药业:是一家主要从事基因工程和生化药物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的高新技术企业,系北京市首家登陆中小企业板的上市公司,是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主要从事基因工程药物的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
长春高新:同时在进行9项产品研发,其中8项涉及基因工程。项目主要瞄准重组人生长激素注射液,以及用于不孕症的重组人促卵泡激素。目前,其长效生长素项目中,用于内源性生长激素缺乏引起的儿童生长缓慢的项目已经申报生产,正在审批。另一款用于不孕症的注射用重组人促卵泡激素,也已申报生产,等待批准。其余6项重组人生长激素注射液仍然处于临床研究,或等待批准临床研究的过程中。
舒泰神:3个研发项目,用于治疗视网膜色素变形的基因药物、用于抗乙肝的小核酸基因药物、用于抗艾滋病的小核酸基因药物,都已经完成部分基础性药学研究工作。
通化东宝:最核心的基因工程项目——Y型PEG化重组人干扰素α2b注射液(I类),已经开始三期临床研究,这是通化东宝最重要的研发项目。公司在生物制药领域,其产品“甘舒霖”填补了国内空白,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丹麦之后能生产基因重组人胰岛素、甘精胰岛素的国家。目前,投资总额为3.5亿元的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重点扶持项目—东宝基因重组人胰岛素二期扩建工程正在紧张引进和安装国外先进设备,公司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人胰岛素生产基地之一。
复星医药:复星医药用于贫血的基因重组促红细胞生成素,以及用于糖尿病的基因重组人胰岛素,也正在研发进行中。公司是在中国医药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上市公司,专注现代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公司抓住中国医药市场的快速成长和中国企业进军世界主流医药市场的巨大机遇,战略性地覆盖研发制造、分销及终端等医药健康产业链的多个重要环节,形成了以药品研发制造为核心,同时在医药流通、医疗服务、医学诊断和医疗器械等领域拥有领先的市场地位,在研发创新、市场营销、并购整合、人才建设等方面形成竞争优势的大型专业医药健康产业集团。
海正药业:海正药业的重组人肿瘤坏死因子受体II-Fc融合蛋白(安百诺),三期临床结束,待药监局批准。公司为中国领先的原料药生产企业,是中国最大的抗生素、抗肿瘤药物生产基地之一,研发领域涵盖化学合成、微生物发酵、生物技术、天然植物提取及制剂开发等多个方面,产品治疗领域涉及抗肿瘤、心血管系统、抗感染、抗寄生虫、内分泌调节、免疫抑制、抗抑郁等。
安科生物:安科生物的基因主导产品重组人干扰素α2b(安达芬)系列制剂、重组人生长激素(安苏萌)、抗精子抗体检测(MAR)法试剂盒(安思宝)均由安科自主研发,目前正在乙肝、肿瘤、白血病生长失败、营养支持、烧伤、免疫性不孕等多种多发病和疑难病的检测和治疗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导产品重组人干扰素、重组人生长激素在国内的市场份额排名均居全国前列,已成功进入了国际市场。
转载自中国第一股票情报聚合平台——云财经网http://yunvs.com
被誉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战歌”的《国际歌》,最早是由谁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呢?有说是瞿秋白,有说是萧三,有说是郑振铎与耿济之合译,但是供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北塔考证,在这些名流大家之前,还有一位无名小辈———列悲,更早地发表了《国际歌》的全译本。那么,究竟谁才是《国际歌》的第一个汉译者呢?
2005年2月,中央编译出版社给我寄来了他们刚刚出版的《寻芳草集》,那是绿原先生最新的随笔集,里面收了《<国际歌>几种文本的比较》一文。那是老先生写于1999年、最初发表于2000年3月24日《解放军报》的文章,原来的题目有点耸人听闻,叫《<国际歌>译文改动真相》。文中说:“中国传唱的中文歌词是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的,译者不详。”绿原先生是现代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过来人和见证者,他应该听说过几位译者的名字,但他说“不详”,应该是有隐曲的吧。这激发了我探讨的兴趣。
瞿秋白说
2005年11月11日的《中华读书报》登载了焦雨虹的文章《<多余的话>:“书生革命者”的困境》。文中说,“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的是瞿秋白。此文是书评,评的是陈铁健导读、选编的瞿秋白作品集《多余的话》。焦的这一论断应该是来自陈铁健。
陈铁健在后来出版的《瞿秋白传》中说,瞿秋白“是最早将它翻译成中文并附上简谱的”。这算是对“正式”的一简短的解释。周永祥著《瞿秋白年谱新编》做了比较详尽的说明,“当时,《国际歌》已有三个中文译词,但是都不合乎唱的要求。他懂乐谱,会弹琴。一边翻译,一边弹唱,苦心斟酌,几经修改,始将《国际歌》歌词成功地译出来。‘英特纳雄耐尔’一词,则照国际惯例保留原音,与乐谱相配。”所谓“正式”指的是瞿译可直接“入乐”。
周永祥又说:瞿秋白是作为《晨报》记者在莫斯科工作期间着手翻译《国际歌》的。回国后,又根据俄、英、法等文本译出了新词,并在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在歌词前,瞿秋白写有小序,说:“此歌自1870年后已成一切社会党的党歌,如今俄国采之为‘国歌’,———将来且成世界共产社会之开幕乐呢。”瞿秋白希望“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同时发表的是他作词谱曲的《赤潮曲》,措辞和曲调明显是《国际歌》的模仿,大概他是要以身作则,使中国的《赤潮曲》和世界的《国际歌》“同声相应”。由此可知,瞿秋白翻译《国际歌》的时间应该是在1922和1923年之间。
瞿秋白是入乐的《国际歌》歌词的第一个译者,这早已是瞿秋白研究的一个定论。
萧三说
那么,绿原说的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国际歌》中文歌词的译者是否就是瞿秋白呢?未必。还有另外一说。《中国翻译词典》说:“1923年夏,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萧三’根据俄文的《国际歌》歌词转译成中文(陈乔年配歌),随后在中国广为传唱的,便是这一版本。”又说:“1939年,萧三在吕骥、冼星海的帮助下,又按照原文对译词进行了修改。其后,他又多次修改,沿唱至今。”这种说法完全符合绿原所说的三个条件,即: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在中国传唱。绿原说“不详”,可能就是因为他无法肯定这位译者到底是瞿秋白还是萧三。他是实事求是而且谨小慎微的。
2001年6月21日,《中华读书报》上祖振声在其文章《音乐出版与涉外著作权》中说:“瞿秋白翻译的1887年由鲍狄埃作词、狄盖特作曲的《国际歌》,于1923年6月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同年,萧三又根据俄文的《国际歌》歌词转译成中文(陈乔年配歌)……”1923年夏,萧三才在苏联开始翻译,而瞿秋白的译文已经在中国发表了。孰早孰晚,还用说吗?
郑振铎、耿济之说
那么,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的到底是谁?
根据上述说法,在瞿秋白之前,“《国际歌》已有三个中文译词”。这三种译本分别出自谁的手笔?它们出现的早晚又顺序如何呢?
据《中国翻译词典》说,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国际歌》开始传入我国。最早的译文刊登在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于1920年10月、11月出版的《劳动者》周刊上(6段诗歌,分4次刊完),题目为《劳动歌》,译者署名“列悲”;几乎与此同时,1920年11月,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办的《华工旬刊》刊出了题为《劳动国际歌》的译文,译者张逃狱。所以,那三个中文译词中的两个应该出自列悲和张逃狱之手,汉译《劳动歌》的发表时间要略早于汉译《劳动国际歌》。据陈福康考证,准确的日期是1920年10月10日至12月5日,分别是《劳动者》周刊第2、4、5、6期。列悲则是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
那么,另外一人是谁呢?
1997年7月16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郑尔康《<儿童世界>和郑振铎》一文,文章后面附录一份介绍乃父郑振铎的“小资料”,说,1920年,郑曾经和“耿济之一起最早翻译了《国际歌》歌词”。郑尔康之所以敢用“最早”一词,是因为他清楚,郑振铎和耿济之的翻译是在秋白之前。他在《石榴又红了———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一书有比较详细的交代:“1920年七八月间,我父亲郑振铎还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一天,他和好友———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耿济之偶然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题名《赤色的诗歌》的诗集。父亲和耿济之把其中的25首诗都读了一遍,一首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弦。于是,他俩商量着要把这些诗都翻译出来,并准备发表在他们编辑的《人道》月刊上。其中《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就是《国际歌》最早的中文译文。”郑尔康所引文字的出处是1921年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面发表了C.Z和C.T“同译”的《第三国际党的颂歌》。据陈福康考证,C.Z即“济之”二字的音译缩写,而C.T则是“振铎”二字的音译缩写。在C.T写的“附注”里说:“在去年七八月的时候……译了第一首《第三国际党的颂歌》。”
被淹没的无名小辈
郑、耿译文到底发表在哪儿?目前有三种说法。一、《人道》月刊,二、《民国日报觉悟》,三、《小说月报》。按照第一种说法,耿、郑的译文发表在1920年8月左右,早于1920年10月10日。但关键是,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它来源于1983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上刊载的郑振铎《最后一次讲话》记录稿,那里面说:“还出了一期《人道》(月刊),上面登过《国际歌》,瞿秋白译意,我写歌词。”瞿秋白当时是耿济之的同学,也与郑振铎过从甚密。郑振铎的晚年回忆显然有误。一是把耿济之的帽子戴到了瞿秋白的头上,二是把发表的刊物误记成了《人道》。1921年9月他自己写的“附注”说得很明白:“而预备登载他们的《人道》月刊也因经济的关系,不能出版……现在先把这篇《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登在本报本号。”《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确实有耿、郑合译的《国际歌》,但据陈福康考证,这是第二次发表,而首发是在1921年5月27日的《民国日报觉悟》。
从发表时间的角度说,哪怕是比较早的1921年5月,也比1920年10月或11月要晚。陈福康在《我国最早的<国际歌>译词》一文中说:“郑振铎等人的这一译作,实是我国最早翻译、而且流传较广的《国际歌》译词”。又说“郑振铎等人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翻译《国际歌》的人。”后来在其专著《一代才华郑振铎传》中也说,郑振铎与耿济之在无意中最早完成了这首被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的歌词的中译!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做了大胆的求证,列悲的译词是从该周刊(指《劳动者》)第二期开始发表的,应是在这年10月翻译的,而从上引郑振铎的说明中知道,他们是在七八月间即着手翻译的。”实际上这个证据也还是一个假设,而且是一个搀杂着先入为主的假设。列悲的译词发表于1920年10月,我们只能说他翻译的时间最晚是在当月,但怎么能武断地说肯定是在这个月份呢?难道不能是9月或8月甚或更早至1919年?
综上所述,对于谁是汉译《国际歌》第一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无法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因为列悲是个小人物,我们几乎不可能从他寥寥无几的传记材料中弄明白他翻译《国际歌》的确切时间。需要强调的是,他那么早就译了,而且译全了。至少从发表先后的角度来说,他的译文比郑振铎、耿济之、瞿秋白、萧三等名流大家的更早,名列第一。但愿无名小辈的这一荣耀不会再因为他的无名而被大人物的大名所淹没。(据《中华读书报》)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jiankang/259325.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douchuanxin@foxmail.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初次性生活后女性阴部会变小吗